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前世今生,艺术永不落幕
雨天,我撑着伞站在香格纳画廊门口,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松香——和2008年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。那时画廊还没装玻璃门,风裹着颜料味直往鼻子里钻,我蹲在未干的油画前看笔触,裤脚蹭到地上的丙烯,回家洗了三遍都没掉色。现在呢?香草拿铁的香气从隔壁咖啡馆飘过来,和松节油味道在走廊里打架,像两个不肯退让的拳击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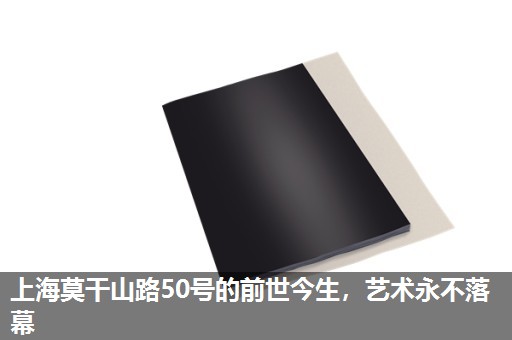
从香格纳出来,我拐进了那条窄巷——你猜我遇到了谁?那个总穿黑衣服的雕塑家,正蹲在铁门边焊东西。铁门锈了。画廊亮了。他抬头冲我笑,指指地上的废铁:“帮房东焊个花架,条件是得留30%的‘工业感’。”我蹲下来看,发现那些铁条被弯成奇怪的弧度,像某种抽象的生物。“2005年我们刚来时,房东也提过类似要求。”他敲了敲铁架,“当时我们用纺织厂的传送带焊了个装置,挂在车间中央,房东看了半天说:‘这算生产工具还是艺术品?’”
2005年:铁锈爬满传送带,艺术在废墟里发芽
2005年的M50,连名字都没有。它还叫“信和纱厂旧址”,或者更直白点——“那片快拆的破厂房”。我第一次来是跟着一群搞行为艺术的朋友,他们说这里有“未被污染的创作空间”。未被污染?那会儿的M50确实够“野”——铁锈爬满传送带,阳光透过破碎天窗在地面投下栅栏状光斑,风一吹,空厂房里全是“呜呜”的回声,像有无数个幽灵在哭。
第一批艺术家是“偷渡”进来的。房东原本打算把厂房改造成仓库,结果被几个雕塑家缠上了。“他们说可以付双倍租金,但得保留至少30%的生产功能。”我后来听老居民说,那会儿房东天天在厂房里转悠,看这群“疯子”到底要干嘛。雕塑家们倒聪明,用废铁焊装置艺术,既满足“生产”要求,又算创作。我见过他们最早的作品——用纺织厂的齿轮和铁片拼成的“机械鸟”,立在车间门口,风一吹,翅膀还会微微颤动。
“那会儿看展要侧着身避开未干的油画,”我蹲在现在的咖啡馆门口,指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对朋友说,“现在要侧着身避开直播镜头。”照片里,几个年轻人正蹲在地上调颜料,背后是斑驳的红砖墙,墙上还留着“安全生产”的标语。朋友笑:“至少现在不用担心颜料蹭裤子上洗不掉。”我摇摇头:“但少了点‘脏兮兮的浪漫’。”
2010年:双年展的分支展,艺术与城市的第一次“公开约会”
2010年的M50,突然成了“艺术圣地”。那年的上海双年展,把其中一个分支展放在了这里。我记得开幕那天,人挤得连传送带都站不下。有个德国策展人站在车间里,对着头顶的吊车说:“这才是真正的‘空间艺术’。”他不知道,那台吊车已经十年没动过了,锈得连挂钩都打不开。
展览最火的是一件互动装置——观众可以踩在传送带上,通过脚下的压力改变前方屏幕上的画面。我排了半小时队才轮到,结果刚踩上去,传送带“嘎吱”一声,差点把我甩出去。旁边的工作人员赶紧跑过来:“别怕!它就是声音大,其实早坏了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那件装置的“互动”功能,全靠工作人员在后台手动切换画面。
但那年的M50,确实“活”过来了。画廊从3家变成12家,咖啡馆从0家变成2家(其中一家还卖酒),连原本的纺织厂食堂都被改造成了“艺术餐厅”。我总记得食堂门口的那块黑板——以前写“今日菜单:红烧肉、青菜、番茄蛋汤”,后来改成了“今日展览:某某某个展”。有次我饿了,想进去吃碗面,结果被保安拦住:“这里是艺术空间,不对外营业。”我指着黑板说:“你们黑板还写着‘红烧肉’呢!”保安愣了下,说:“那是以前的,现在只卖艺术。”
2020年:疫情下的自救,艺术在玻璃窗里跳舞
2020年的M50,安静得可怕。我三月去的时候,整条街只有两家画廊开着,一家是香格纳,一家是某个独立空间。香格纳的玻璃门上贴着“请保持距离”的告示,展厅里只有三件作品——两件雕塑,一件视频。视频里,一个女人在空荡荡的厂房里跳舞,背景是破碎的天窗和生锈的铁架。我站在展厅里看了十分钟,突然觉得那女人跳的不是舞,是在和这个“被按了暂停键”的世界对抗。
独立空间的主人是个年轻策展人,她把展览搬到了玻璃窗里。“反正没人进来,不如让路过的人看。”她在窗边摆了五件小雕塑,每件都配了手写说明牌。我蹲在窗外读,读到第三块时,她突然打开窗递给我一杯热茶:“外面冷吧?”我接过茶,发现她的手指上沾着陶土——原来她还在做陶艺。“疫情让很多人离开了,”她指着对面的空厂房,“但也有新的创作者搬进来。昨天有个做数字艺术的男孩问我:‘这里能接网线吗?’我说:‘能,但网速可能不如你家。’他笑了:‘没事,我需要的是这里的氛围。’”
那年的M50,最火的不是展览,而是“窗展”。艺术家们把作品摆在窗边,路人可以随时停下来看。有位画家甚至在窗上贴了张纸:“拍照请关闭闪光灯,否则下次展览改办行为艺术。”我后来又去了三次,每次都有新发现——第一次看到的是荒凉,第二次是生机,第三次是妥协。妥协什么?大概是妥协于“艺术必须被看见”的现实吧。
2023年:咖啡与闪光灯,艺术在妥协中生长
现在的M50,像个“混血儿”。画廊和网红咖啡馆共享同一栋楼,数字艺术工作室与传统陶艺坊挤在同一层,穿汉服的姑娘和戴耳机的男孩在走廊里擦肩而过——你懂那种感觉吗?像两个平行宇宙突然撞在了一起,然后慢慢融合。
我特别喜欢二楼的那家咖啡馆——不是因为咖啡好喝(说实话,香草拿铁甜得有点过分),而是因为它的位置。它开在原纺织厂的车间里,天花板上还挂着生锈的吊钩,墙上贴着“安全生产”的标语,但桌椅是北欧风的,音乐是爵士的,连菜单都是手绘的。有次我点完咖啡,问服务员:“你们怎么想到在这里开咖啡馆?”她笑了:“因为这里‘有故事’啊。”我点点头——确实,这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根铁管,都藏着故事。
但故事多了,矛盾也多了。最明显的是“游客打卡潮”。现在来M50的人,十有八九是来拍照的。他们举着自拍杆在画廊里转,对着作品摆各种姿势,闪光灯“咔嚓咔嚓”响个不停。有位画家受不了,在作品说明牌上加注:“拍照请关闭闪光灯,否则下次展览改办行为艺术。”我见过最夸张的一次——一群女孩围着一件雕塑,轮流拍照,拍了二十分钟还不走。保安过去劝:“姑娘们,后面还有人要看展呢。”她们头也不抬:“我们买票了呀!”保安无奈:“但你们挡着别人了。”她们这才不情愿地挪开,嘴里还嘟囔:“艺术不就是给人看的吗?”
艺术确实是给人看的,但“看”和“消费”,是两码事。我后来又去了三次,每次都能看到新的“打卡点”——某面涂鸦墙、某件装置艺术、甚至某家咖啡馆的窗户。有次我站在涂鸦墙前拍照,突然听到旁边两个女孩聊天:“这面墙好上镜啊!”“是啊,比那些画展有意思多了。”我放下手机,突然有点难过——不是因为她们不喜欢画展,而是因为她们把“艺术”简化成了“背景板”。
但转念一想,也许这正是M50的“生命力”呢?它不再是一个“纯艺术空间”,而是一个“艺术与生活混合体”。游客的“朝圣式参观”,确实会打扰创作,但也会倒逼艺术家创造更尖锐的作品——就像那个在说明牌上“威胁”观众的画家,他的新展览,我后来去看了,确实比以前更“狠”了。
那些“勾肩搭背”的商业与理想
我曾吐槽M50太商业化,直到在某间阁楼发现一位老画家用退休金资助年轻创作者——原来商业与理想可以这样勾肩搭背。那间阁楼藏在三楼最里面,门牌号已经模糊不清,我推门进去时,老画家正在给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上色。他抬头看我,笑了笑:“随便坐。”
阁楼里堆满了画——未完成的、完成的、被退回的、被收藏的。老画家指指墙角的一堆画框:“那些都是年轻创作者的,我帮他们装裱,不收钱。”我问:“为什么?”他想了想:“因为我年轻时,也被人帮过。”他讲起1980年代,他在纺织厂当工人,下班后偷偷画画,被一个老师傅发现了。“老师傅没骂我,反而给我找了个小仓库,说:‘你在这儿画,没人管。’”他顿了顿,“现在轮到我帮别人了。”
从阁楼出来,我拐进了那家卖陶艺的工作室。老板是个年轻女孩,正在拉坯,手上沾满了陶土。“您看这个,”她举起一个未完成的杯子,“我打算在杯底刻一句诗。”我问:“什么诗?”她笑了:“‘艺术永不落幕’。”我愣了下,突然想起2008年第一次来时,那个雕塑家说的:“我们不是来拯救这里的,我们是来和它一起活的。”
尾声:那朵像梵高《星月夜》的云
走累了可以去“老吉士”坐坐,我每次带外地朋友来,他们总说这里的红烧肉比画还下饭。从餐馆出来,天已经黑了,M50的灯一盏盏亮起来,像星星落在了地上。我沿着窄巷往回走,突然听到一阵笑声——一群中学生正围着一面涂鸦墙讨论,有个女孩突然喊:“快看!这朵云像不像梵高的《星月夜》?”
我停下脚步,抬头看。那朵云确实像——漩涡状的,带着点疯狂,又带着点温柔。女孩的同学们纷纷掏出手机拍照,闪光灯“咔嚓”一声,惊飞了墙角的几只鸽子。鸽子扑棱着翅膀飞向天空,像一群黑色的音符,在夜色里划出优美的弧线。
艺术永不落幕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它不在画廊里,不在咖啡馆里,不在游客的镜头里——它在每一朵像梵高画的云里,在每一个被资助的年轻创作者的笔尖上,在每一个和老厂房一起活着的人心里。
推荐下午4点后参观,光线最适合拍照——但别只拍照,多看看那些画,多听听那些故事。画廊周通常在每年5月和11月,那时候的M50最热闹,但也最“真实”。附近有家本帮菜馆,红烧肉配艺术,绝了——不过记得,吃完别把油蹭到画上。







